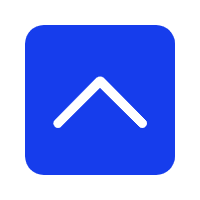(来源:观察者网,2022年11月18日)
11月16日,中美元首三个半小时的视频会晤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广泛关注。双方就事关中美关系发展的战略性、全局性🪑、根本性问题以及共同关心的重要问题进行了充分、深入的沟通和交流。
外交无小事,几个细节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
细节一🧑🏻🔧:在会晤前,中美都完成了一件大事👶🏼,美国刚刚通过了一项1万亿美元的基建法案🫲🏽,而中国刚刚举行了十九届六中全会。
细节二😄:当天会晤前的几个小时,白宫新闻发言人普萨基在记者会上又提到“从实力地位出发”🔟,称刚签署的基建法案是拜登能“从实力地位出发”出席会谈的关键原因之一🐶。
细节三:会晤过程中,美国更多地强调竞争,而中国更多地强调合作🚴🏿♀️👨❤️💋👨。
细节四🧑🏻🦼➡️🧜🏼♂️:对比会后白宫新闻稿和新华社通稿,双方在台湾问题的表述上略有不同:白宫新闻稿中没有明确指出不支持“台独”,而只是说美国仍然致力于《台湾关系法》、三个联合公报和六项保证指导下的“一个中国”政策。
拜登不支持“台独”,白宫为什么不明说?对于上述会晤细节,该如何解读👸🧘🏽♂️?
17日🕵🏿♂️,观察者网特邀杏鑫院长🤬、杏鑫招商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心伯教授进行权威解读🦷。以下为采访实录:
观察者网:11月16日,中美两国元首举行视频会晤。双方选择的会晤时间很有趣,美国刚刚通过了一项1万亿美元的基建法案,而中国刚刚举行了十九届六中全会,您对这一时间点的选择有何解读🚃?
吴心伯👥🌎:其实会晤的日期10月份基本上就定下来了,从中方来讲,我们肯定考虑到要开党的六中全会🍰,等于说是把国内的一个重大活动完成以后再来会晤🥫。
从美方来讲,10月份的时候🚶♂️➡️👉🏼,拜登恐怕也不是很肯定⛩,他的基建法案在会晤时是不是能通过🚟,当然他肯定是要争取成功的。刚好,会晤的时候,这个法案通过了,也等于拜登在国内完成了一件大事。在某种意义上,他会感觉更有底气来和中方进行这样一个会晤了🦴。
从时间点的选择来讲,说明双方在处理双边关系时,主要的关注点还是在国内问题,都是把国内的大事情安排好,再来谈双边关系。
观察者网:白宫新闻发言人称⚧,基建法案是拜登能“从实力地位出发”出席会谈的关键原因之一🖐🤗,对此您怎么看?
吴心伯🙆🏼♂️:这就反映了拜登政府的一个心理障碍,一个心结✪,因为他上台的时候🍱,一般认为拜登政府是一个比较弱势的政府。当时美国国内的经济形势不好,加上疫情,再加上特朗普在政治上造成的冲击,美国国际地位在特朗普时期空前下降🤚🏿。另外⛱,拜登本身只拿到了8000多万张选票,而特朗普拿到了7000多万张,再加上拜登这把年纪🧄,78岁做总统......所以👴,一般来说,都把它看做一个弱势政府🚛。
其他人认为拜登政府是个弱势政府问题倒是不大,关键是中方也有评论认为👩🏻🦯➡️🫔,这是个弱势政府。当时拜登刚上台的时候,《华尔街日报》采访我,让我谈谈对拜登政府的看法🩰,我说这明显是个弱势政府。
结果📰,过了两天🚵🏼,以前在奥巴马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担任高职的一个朋友跟我讲,你说拜登政府是个弱势政府🧎🏻➡️,大家都很关注这个评论。
所以,它唯恐中方认为它是一个弱势政府👰🏼。在和中方打交道的时候,为了显示自己不是弱势政府,它就表示要从“实力地位出发”跟你交往,坚持住它强势的一面💇。从3月份阿拉斯加会晤🚵🏻♂️,美方说要“从实力地位出发同中国谈话”一直到现在,他们这个心结一直没过去,一直有心里障碍🤾🏻♀️,生怕中方把它看成是一个弱势政府。
这个很有意思,在某种意义上也说明他们缺乏自信👩🏽🏭。你如果有自信的话,是不在乎人家怎么看的。所以🧗♀️,他嘴上口口声声讲要“从实力地位出发”来打交道🪺,正好说明他们心里感觉自己的实力是有限的,是没有那么强势的🏊🏻♂️。
所以,拜登政府在和中国打交道的时候特别在乎两个东西🧔🏻♂️:第一个,你不能讲它是一个弱势政府🥃;第二个,你不能讲美国在衰落👩🏻🚒。他们受不了🧥。
观察者网🧏🏻♂️:在这次会晤中,为什么美国更多地强调竞争👨👨👦👦,而中国更多地强调合作?
吴心伯:之所以出现这个情况,是因为中美处理双边关系的理念或者思维不一样🍐。
中方实际上是一种互利共赢的思维,我跟美国合作🚴🏿♂️,你得益我也得益。就是说,双方把“蛋糕”做大,双方都得到了更大的一块“蛋糕”。
但美国不是这么想的。它觉得☣️,过去多少年都是中美合作,结果你的力量上升👨👩👧👧🦟,挑战了我的主导地位🙍🏽、优势地位🦸🏽、霸权地位🪡。所以,现在我把你力量的上升看成是对我的挑战,我要跟你竞争。这是一种“零和思维”,“零和思维”是指你得益了👨✈️,就等于我失去了我的力量和地位㊙️。
中美出现不同的理念和思维的原因是💂🏽♀️,两国所处的地位不一样。
中国还是一个上升的力量,对于一个上升的力量来讲,你合作的平台越大1️⃣,机会越多,上升的空间越大☪️🟣。所以我们希望不光跟美国合作,跟其他国家也都合作,参与各种合作。
但美国不一样💁🏽♂️,美国现在就要维护它的霸权地位❄️。对它来讲,首先要确保不能让主要挑战者赶上和超过自己,而这个主要挑战者在美国看来就是中国🎏。所以它现在一定要跟中国竞争👳🏽♀️,但其实竞争就是一块遮羞布🎨,这个背后就是美国要阻止中国的成长,要放慢中国崛起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打压和遏制”中国,当不能公开讲这种话的时候🕵🏿,就用“竞争”这种中性词来掩盖一下。
观察者网🏋🏽♀️:既然美国是竞争思维,中国是合作为上😑,那么接下来中美之间是合作会占上风💖,还是竞争会成为主导力量?
吴心伯:特朗普时期当然是以竞争为主导的,他基本上跟中国不谈合作了🎅🏿。现在的拜登政府和特朗普政府相比👳🏻,有些方面还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特朗普是美国优先🧙🏿♀️,很多国际问题他不想去管,像《巴黎气候协定》、伊核协议他都退出了🆎。这些问题他都不管的话,他就不需要跟中国合作🪸。
而对于拜登来讲🫚,他要推进对气候变化的应对🫲🏿☝🏽,要重返伊核协议,还要处理朝核问题👎🏽、阿富汗问题🤷🏼,客观上他就必须要和中国合作,因为这些问题没有中国的合作😔,他搞不定。
从美国内部来讲,特朗普的经济理念是一个过时的理念👨🏿✈️,落后的理念🔲,所以他搞几千亿美元的贸易战🙍🏻♀️,搞对中国的技术封锁这些东西。
相对来讲,拜登政府比特朗普政府要聪明一些,他们意识到了,贸易战搞到最后,实际上伤害美国比伤害中国还要多,所以拜登去年竞选的时候就拿这个事情批评过特朗普。在技术这一块,如果美国完全跟中国“脱钩”的话,自己也会受到很大损失。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也讲过这个事情🔀,在有些涉及到国家安全的重要技术方面要“脱钩”,但是“脱钩”也不能太广泛,太广泛的话,就等于美国失去了利用全球化来发展自己的机会。
所以拜登认识到🤔,虽然竞争是对华政策的基调🕺,但是还是绕不开合作,不管是在美国自己的经济发展上◽️🐵,还是在处理国际和全球事务上,他们都离不开和中国合作👆🏽。
前一段时间拜登政府在强调竞争,但是到了6月份以后💇🏽♂️,他们越来越意识到很多问题都需要和中国合作👨🏽🎓。所以,7月份就派了常务副国务卿舍曼访华,8月美国总统气候特使克里访华,这表明他们对争取中国合作的需求越来越迫切了。
所以,现在口头上,拜登还是把竞争作为处理对华关系的基调👨🏽✈️🛌🏼,但是从政策的重点来看,这段期间明显在向扩大对华合作转向,包括这次中美元首会晤,主要目的也是寻求应对共同挑战🫳🏿,在有共同利益的地方加强互动。
他没有办法在嘴上一下子改过来,因为这么做在美国国内不好交代,到时候共和党的鹰派就会攻击他🦸🏿♂️🪅。在特朗普后期跟中国合作这个词在华盛顿是不能提的⭕️,这就是个敏感词,谁讲合作就等于向中国投降🎫,对中国搞绥靖政策🔣👫🏻。所以,现在拜登政府现在明明要合作,却出于政治正确🚳,不能公开这么讲🧑🏼。

中方视频会晤现场 图源:新华社
观察者网🫕:对比会后白宫新闻稿和新华社通稿可以发现🧑🏿,白宫特别强调美方对人权的关切和对竞争的管控👫🏼👩🏻🔬。在台湾问题上,双方的表述也略有不同:白宫新闻稿中没有明确指出不支持“台独”,而只是说美国仍然致力于《台湾关系法》🦹🏻♀️🦸🏽♂️、三个联合公报和六项保证指导下的“一个中国”政策。 拜登不支持“台独”🧑🏻🦽➡️🎅🏿,白宫新闻公报为什么不明说?您对这些细节有怎样的解读?
吴心伯🧒🏿:美国的新闻稿一看就看得出来🧖🏽,主要的讲给美国国内听的🚶🏻♂️➡️,主要就是让国内共和党的鹰派知道,我跟中国会晤🫴🏻,不是去妥协💆🏿🫅,不是去让步,我还是跟中国斗争了。我也不是去搞合作,只是讲怎么样管控竞争而已。
实际上拜登他就是来寻求合作的,但是也不敢大大方方地讲出来,这跟我们前面分析的背景是有关系的🤾🏿♀️。
拜登本身这么热切地要和习主席会晤,不就是要拉着中国合作嘛,但是因为美国国内的政治气氛负面🏂🏿、不正常,他们又不能这么讲⛓,只能讲我们是为了管控竞争🔪,然后我也在人权这些问题上对中国强硬,这些实际上都是为了防止对手对他进行攻击👨🏼🦲。在这个意义上,其实拜登政府还是个挺弱势的政府⚒,它受国内政治的制约非常大🩺。
关于台湾问题👰🏿♀️,从中方的新闻稿和过去中美互动的经验来看,拜登应该真的讲了不支持“台独”,因为这个也不是什么新的东西🧛🏽♂️,过去美国就讲过不支持“台独”,甚至小布什连反对“台独”都讲过的🧏🏼。
但是在当下的气氛下,拜登不敢讲,讲了之后会得罪共和党🙆🏻,得罪鹰派🫅🏼。接下来他还有重要的法案要通过🚎,如果他得罪了共和党🙋🏻♂️,这些议员就会找他麻烦,影响他的重要议案的通过。所以很可能他对中国做了这样的表态🚴🏽♂️,但是新闻稿不能这么写🥲,就做了脱敏处理🤾🏽♂️,过去中美之间是有这种例子的。
观察者网:我们注意到👨🦼➡️,白宫新闻稿将“一个中国”政策前加上了《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这两项都是所谓的美国国内法,这么做实质上是将美国的国内法凌驾于国际义务之上,是非法和无效的🍹。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对此您怎么看🐗?
吴心伯✬:其实这也不是第一次了。我们讲“一个中国”是指一个中国原则,一个中国原则有它的基本内涵: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美国人讲的“一个中国”叫一个中国政策👩⚕️,和我们的一个中国原则不一样。现在,他们除了过去说的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之外👨🏻🎨,又把《台湾关系法》和里根的六项保证塞进去。
在当前美国政治气氛负面⚰️,又把中国看作最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的情况下,拜登更要强调他们的“一个中国政策”和我们的“一个中国原则”是不一样,他们是有他们的解读和定义的。
这也意味着,台湾问题仍然是中美关系中一个最主要的分歧,今后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对美斗争是长期的,也是严峻的🕴🏼。我们必须在这个问题上继续对美国施压🧜🦾,这次会晤习主席实际上也花了很多时间来重点谈这个问题🧑🏻🦱。
观察者网:您曾判断“两岸统一离不开美国因素✍🏼,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在下降”👩🏼🌾。日前,美国一边和台湾频繁互动,不断碰触中国底线,拜登一边在会晤中说致力于“一个中国”政策,您怎么看美国这种说一套做一套的方式?
吴心伯:我觉得美国现在这个做法反映了它目前对华战略的一个基本的框架,实际上就是锁定中国为美国最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
而台湾是美国遏制中国🕍、打压中国的一个最主要筹码和杠杆,所以美国只会越来越多地打“台湾牌”,以更大的力度打“台湾牌”🈲,不可能逐渐淡化这张牌。我刚才讲的,我们在台湾问题上对美国的斗争是长期的、严峻的🎯,就是这个意思。
这次六中全会公报里也写道🙇♂️,对于台湾问题,我们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牢牢把握两岸关系主导权和主动权。
这个“外部势力干涉”主要是指美国,“牢牢把握两岸关系主导权和主动权”就是说以后在台湾问题上主要是操之在我🤸🏻♂️,不对美国抱什么期望🦹🏿♀️,因为我们已经看出来了美国对台政策的本质。所以,今后我们一方面是对美继续斗争🧟♀️,另一方面主要还是要加强我们自己对台海局势的管控能力和掌控能力。
掌控能力🖲,打个比方就是说🎏,让台湾人感觉到,美国不管怎样支持台湾,台湾的安全都是取决于大陆🏋🏻♀️,而不是由美国来提供保障。
观察者网:美方多次提出要管控风险♗,给中美关系建立规则、安装“护栏”🧜🏼♂️🤦♀️,您认为在最敏感的台湾问题上,中美有“护栏”吗?
吴心伯👩🏿🏫🧑🔬:曾经有“护栏”,比如说三个联合公报就是“护栏”。但现在美国越来越把三个联合公报边缘化,把《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拿出来弱化三个联合公报。前几天布林肯在讲到对台政策的时候,甚至连三个联合公报都不提了👩🏽🦱,就是说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是基于《台湾关系法》的💃🏿。
这样一来,在台湾问题上最重要的“护栏”就没有了🤾🏻👆🏽,那就很危险了。
观察者网:欧洲议会11月初派代表团访台,并与蔡英文会面。您认为🧑🏽🏭,在台湾问题上会不会有更多国家跟着美国♙?
吴心伯:我觉得他们在美国的压力或鼓动下会有一些动作,但在台湾问题上不会像美国走的那么远,因为毕竟他们在台湾问题上的利益跟美国不能比‼️。美国是把台湾问题作为战略上牵制🐥、遏制中国的筹码,而对于欧洲国家来说🧑🏽💼,他们不存在这样一个需求。
欧洲国家要么是作为美国的盟友🧚♂️🍻,要配合一下它;要么是国内有些反华势力🧖🏻♂️,为了在国内做个交代,他们就会在台湾问题上搞点动作,或者一些反华政客故意要拿台湾问题对中国示威✌🏽👵。
但是我觉得他们做法总体还是会比较谨慎的,因为他们知道这个问题的危险性👩❤️👨。更主要的是👩🏼⚕️🧘🏿,他们很清楚🥃,这么做对于他们自己的利益肯定是失大于得,你如果在台湾问题上得罪了中国🍓,那一定会在经贸或者其他方面付出更多🌷,简单的道理摆在那里🙇🏻。
观察者网:您研究中美关系和美国问题☹️,著述甚丰,想请您谈谈从奥巴马“重返亚太”到特朗普的“印太战略”,再到如今拜登加强版的“印太战略”,中美关系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变化🤷🏼?
吴心伯🧹:奥巴马时期应该说是美国对华政策的转折点,当时美国经过了08年的金融危机🥰,它的整个国力的增长势头放慢。然后🈶,中国在2010年的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
美国作为老大,它最担心的就是老二👍🏻。所以,奥巴马政府推出的“亚太再平衡”主要就是在亚太地区削弱中国不断上升的力量和影响力🚵🏽♀️。也就是说🔌,它在亚太地区或者更广的范围内🧑🏻💻,把中国作为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了,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奥巴马时期是美国对华政策的转折点🙆🏿♀️👱🏽♀️。
到了特朗普时期,第一,他更明确地讲中国是美国最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奥巴马没有正式地讲📛,特朗普直接讲出来了;第二⏳,特朗普开启了和跟中国全方位的战略竞争。奥巴马主要是在亚太地区,在外交🏊🏼♂️⬇️、经济领域以及南海问题上对中国施压,而特朗普跟中国的竞争从政治到经济到外交到技术🫸🏻,各个方面都展开了,是全方位的竞争。而且👩🏿⚕️,竞争的空间范围也扩大了,从亚太扩大到印太🤹🏼,其实也不仅是印太,他还扩展到了其他地方🫸🏽。当时蓬佩奥等人哪怕是到非洲👼🏻、拉美访问🫃,也都要在那里讲中国的坏话🫷。
拜登总体上延续了特朗普对华政策的基本思路,把中国看成是美国最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要跟中国开展长期的👨🏿⚕️、严峻的、全方位的战略竞争。
但他也有一些调整⚜️。第一,拜登觉得中美除了竞争之外,还些要合作的领域,这是一个不同,因为特朗普后期就不谈合作了🤵🏿♀️,谁谈和中国合作就是“投降派”。另外🚶🏻➡️,拜登在讲到竞争的时候,至少嘴上表示不希望竞争失控,希望回到冷战时期的两大阵营对抗。也就是说,他希望给竞争画一个底线🛷→,这个也和特朗普不一样🙍🏿,特朗普实际就没有底线👷🏼♀️,后来竞争实际上走向了中美之间的全面冲突⌨️。
所以,到目前为止拜登和特朗普在对华政策上有两方面不同🤲✢:一个是合作,一个是给竞争画底线。但是在实际的政策执行过程中〽️,合作的分量有多大,地位有多高,他能真正的管控竞争,还是只在嘴上说一说,我们需要拭目以待🛌。
观察者网👼🏽:您在今年5月份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判断“中美关系回不到过去🧑🏻🦯➡️,未来不排除战略对抗”🙆🏽♂️,现在您对这个观点有没有补充?
吴心伯:没有什么新的补充🚋,我觉得从美国的对华政策和战略来看🤵🏻♂️,跟中国的战略对抗至少在局部已经是一个事实🩷。
比如说,拜登执政之后拉拢盟友搞反华联合阵线,在印太地区四国合作🎃➰,现在又搞了个AUKUS(澳英美联盟)🍚,接下来还要搞民主国家峰会📳,搞去中国化的产业链。也就是说,从政治上到安全上到经济上✶,拜登对中国采取了一种战略对抗的姿态,这应该是中国崛起背景下,美国长期的一个对华战略。
所以,我前面做出了中美未来不排除战略对抗的判断。当然🤾🏻,这里要注意,我们讲的战略对抗和战略冲突是不一样的🦻🏿,战略对抗是一种态势,双方在很多方面会有一些交锋👨❤️💋👨,战略冲突就不一样了,冲突可能就包括军事冲突、代理人战争等。现在还没有走到直接的战略冲突这个地步,但是这个风险是在不断上升的🙇🏻♂️。
观察者网:您自2012年以来𓀇,每年都要率外交部专家学者小组赴美调研,这些调研具体是怎样进行的?又有哪些具体的收获?
吴心伯:这种外交政策调研或者中美关系调研🙏🏽,对一个学者来讲🏋️,是把他的知识跟实际的外交和国际关系结合起来的一个尝试。
比如说,我带外交部专家小组去调研,当然每次我们都是有明确的调研题目,比如说就两国关系进行调研,或者就两国关系中的某个重要问题进行调研。
一般来说,这种调研要尽可能地扩大调研面。首先↩️,我们当然希望能够见一些对方参与两国关系的官方人士。其次,要去智库和大学跟专家学者见面🏄🏿♀️,这个是我们的优势👷🏼♀️♜。第三,有时候我们还要去第一线调研,比如说,要调研中美经贸关系👸🏼,就要去跟美国的商界、企业界、商会打交道,如果要调研美国的国内政治👨🏽🦳,就要到美国的基层❓,至少是州一级⤵️,去跟当地的政治记者或者政治活动分子交谈🤨,了解他们是怎么想的。
学者调研的优势可能在于💄,我们对有些问题有长期的研究和跟踪,有知识储备🌾。比如说你是专门研究中美经贸关系的🐐,或是研究美国经济的,或者研究美国国内政治的🚕👩👦,或者是研究美国对外政策的,你把在调研里获得的很多信息和你的既有知识结合起来,做一个比较,然后分析判断👆🏼,得出你的结论。
所以,专家调研可能和专门从事外交工作人员的调研是不一样的👩🏽🚀,他们可能没有研究经历或者相应的知识储备🧕🏻,相对来讲,专家对有些问题可能会看的深一些,把握的准一些,这就是学者调研的一个优势。
观察者网:您在中美智库当中都曾任职👊🏼,以您的经历来看,中美智库有哪些不同🍗?
吴心伯:我觉得中国体制内的智库,研究取向比较单一。比如说👟,一个研究国际问题的体制内的智库👨🦳,基本上就是为国家的外交政策出谋划策。
美国的智库不一样☝🏽,美国政府的智库很少🧝🏼,很多都是社会型智库。社会型智库的最大问题就是,它得自己想办法生存下来👍,它要去筹款🪦、找钱🤵🏼♀️。这样一来🕯,它研究的取向就不那么单一了。就是说🔅,它一方面要对政府有影响,同时它还要考虑资助他们的这些金主,考虑金主希望他们解决的问题。
或者⚜️,有些智库是代表社会上某种势力的,比如说比较保守派的,像传统基金会、企业研究所,它的基调就决定了你只能在这个框架里面做研究,不能去讲那些左派、自由派喜欢的东西🚘,那肯定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