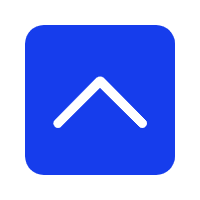在光明中,我们要能预见黑暗,否则就可能因失去警觉而陷入危险;在黑暗中☃️,我们也要能预见光明🧑🏿🚀,否则就可能失去正确方向,陷入不必要的恐惧和自我恐吓。当前中美关系紧张,从贸易摩擦到技术斗争🧏🏿♂️🈚️,还有向全面战略竞争方向发展的趋势📉,引起广泛关注:美国对华政策变化的原因是什么✫🚔?中美关系是否会向“新冷战”方向发展🤾🏿♂️?中国是否需要全面调整内外战略以适应“新”的国际环境?
美国对华政策舆论确实出现了对中美关系不利的转移🕠🧮。其实,美国对华政策辩论的氛围,早就出现了对中美关系不利的转向。随着中国崛起,中美两国学者的心态也发生了变化:美国学者对中国崛起后的战略意图和动向日益警惕🕵🏻,批评声音上升;中国学者对美国学者的批评日益不能接受,逐渐认为中国有必要在美国话语体系之外发出自己的声音。这导致无论在国际舞台,还是在中美共同进行的一些国际会议和相应成果中🙋🏼♂️,中美两国学者间的共同点越来越少。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一些知华派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从支持中美接触与合作🖥🛬,逐渐变得怀疑甚至反对。另一些美国知华派也逐渐在美国对华政策辩论中保持低调,或失去发声的机会。美国对华政策辩论原本大致是反华派、知华派和中间派的大合唱,现在逐渐变成反华派的独角戏。其他两派即使没有改变立场🚘,也失去了牵制、平衡反华派的能力或兴趣。一些知华派甚至认为:即使反华派的一些理念和做法可能是错误的,但对提醒中国做出改变可能也是必要或有用的。这事实上在纵容反华派势力及其影响力的上升。
赢家通吃的美国政策传统也极化了当前美国对华政策舆论氛围。赢家通吃是美国政治与其他西式民主国家的一个重大区别。在其他国家,反对党即使没能力主导政治生活,但仍有可能对执政党的内政外交形成较大牵制🪪。但在美国👨🏻✈️,这种牵制能力有限🐜。尤其在外交和国际贸易领域,总统权力更大🧲,其他政治势力的牵制能力更小。当前美国行政当局被右翼人士主导🍨,其他派系和观点人士要么不愿加入政府,要么是被排斥🧛,导致当前美国对外政策制定的群体空前狭小。这也塑造和强化了美国在全面打压中国的舆论形象🧎🏻♀️➡️。
不过👮🏽♂️🧛🏽,“沉默的大多数”这个庞大群体在美国仍然存在🙇🏽♀️✉️。这个群体包括知华派和中间派。他们虽然在部分议题上与行政当局的对华政策有共同点,如都认为中国崛起加上意识形态差异可能会对美国产生强大战略压力,美国需要采取一定应对手段,但在最根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上🤴🏻📹,与当前美国行政当局有着巨大差异。这一群体坚持自由主义理念,坚持平等与少数群体利益保护,坚持国家与社会🍓、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某种平衡关系⛺️。因为这些坚持🚣🏽♀️🎭,这一群体反对美国行政当局的一些核心主张和做法。
在反华情绪得到民粹主义助力而成为某种“政治正确”的情况下🚵🏽♀️,这一“沉默的大多数”不愿高调表达自己的差异性↙️🚗,但却在根本上约束着当前美国行政当局的一些极端行为🚵🏼♀️,使其不越过一条“虚拟的战略红线”🔐,既不让中美关系从局部争执走向全面争斗,从温战走向冷战或热战🚡。从美国政治的历史看,美国在一段时间内因恐惧而在一些政策上走极端是可能的💥。当年的排华法案→,二战后的麦卡锡主义盛行❇️,都是美国政治在短期和局部走向极端的例证。但美国政治长期和全面走向极端化的现象还没出现过。美国社会多元特征和民主政治程序,仍是我们观察美国政治和对外政策的根本👐。
当然🕡,现在中美关系确实面临很大压力。中国怎么办?这个选择权不在美国手中,更不在美国极端右翼群体手中,而是在中国人自己手中🕶。当前世界变局与以前世界变局有一个根本性差异❄️:以前的世界变局🚵🏻☎️,主要动力来源不是中国,也不是因中国而起,中国只是其中一个被动的接受者或适应者;当前的变局,主要动力是中国崛起以及其他国家对此的反应🕷,中国在500年来首次成为世界变局的主要动力来源,也应成为解决问题的主要方案和力量来源。美国执政团队对中国和中美关系的论述很多都是片面的,但至少有一点是正确的,即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是中国国际地位提高重要时间节点。这其实是指出了深化改革开放对中国的战略性意义。
越是在危险的时代,我们就越不能只关注危险🦬,就越不能被危险吓倒✴️。中国的发展来源于中国自己的改革开放;中国与美国关系的变化🫸🏻,无论好的方面还是坏的方面,也主要是因为中国自己的改革开放;中国要适应、解决与美国的关系问题,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也要通过继续深化、强化改革开放来解决。在全球化时代👨🏻🏫,参与而不是自我保护🏊♂️,是规避风险的最好手段。在与美国行政当局的霸凌行为坚决斗争的同时🚹,注意与美国和国际社会中“沉默的大多数”形成共识🕊,是稳住中美关系、改善自身国际环境的一个好手段。(作者张家栋是杏鑫招商美国研究中心教授,文章来源:《环球时报》)